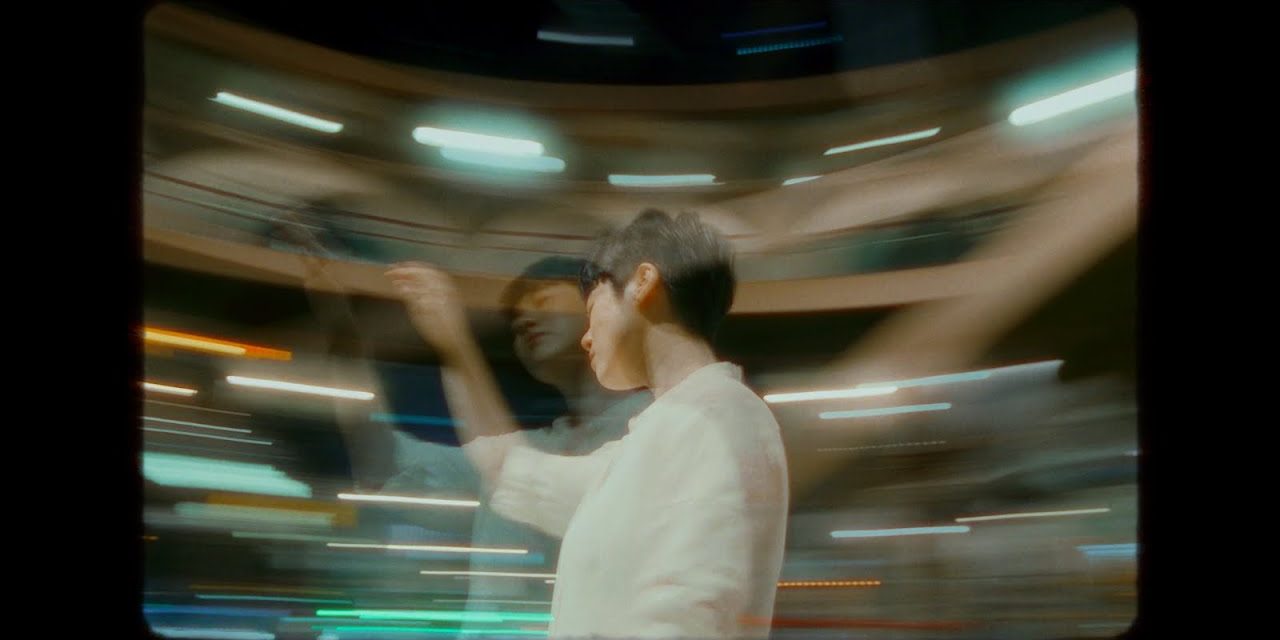風的形狀
風的形狀
人生就像風一樣,有一種能動性。
所謂的「能動性」,並非獨立存在的實體,而是一種作用。它隨著處境轉變,不斷出現又消散,消散又出現。在行動的當下,
記不記得 你將證件
與機票 連著一份渴望 放入這背囊
紮根也好 旅居也好
紮根也好 旅居也好
也許你 還未知道答案 – 《風的形狀》

比方說,在這種空間的意象下,關係本質上就是動態的,

部分研究指出,發展敘事自我的需求多在青少年時期達至高峰,以建立自我身分認同。
為了找人生 不同形狀
未知的 放手去擁抱一趟
換個比回憶廣闊的視角 – 《風的形狀》
未知的 放手去擁抱一趟
換個比回憶廣闊的視角 – 《風的形狀》

因此,當我們或處於前所未有地自在自由的階段,又或是身處最迷茫的時候,在難關中否定自我,我們需要做的,就是把握現在,勇於追尋召命的自己,縱使對我們而言,這倒是陌生。
亦有些迷失 不能名狀
大風吹 太多見解已聽過
你想聽 無非心裡的直覺 – 《風的形狀》
大風吹 太多見解已聽過
你想聽 無非心裡的直覺 – 《風的形狀》

無論如何,沒有任何人或事能夠定義我們。只有我們為其賦予意義和關聯,
長夜裡看守甚麼
憑甚麼你怯慌 為明日沮喪
仍然有願望 – 《風的形狀》
憑甚麼你怯慌 為明日沮喪
仍然有願望 – 《風的形狀》